1977年的寒冬来得比往年更凶刚进腊月迎新街道就被北风卷着的雪片子糊了层白。
这条夹在解放路与防修路之间的巷子两侧砖墙早被岁月啃得坑洼墙根堆着半融的雪踩上去咯吱作响倒像是谁在暗处咬着牙。
我接到马文书通知时正对着窗台上冻裂的墨锭发呆——那是去年冬天用省下来的粮票换的此刻裂成了三瓣像极了我这条不听使唤的右腿。
“小张街道有活儿找你。
”马文书托人传话过来。
我听后兴奋之余心里有些坦突不安。
自从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之后没能跟上上山下乡的队伍我就成了巷子里的“闲人”。
母亲下班后经常往街道跑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回来总说“王大庆书记爱人今天看我眼神和善了些”可我知道作为一名残疾人连走路都费劲哪配占个工作名额。
裹紧棉袄出门时风像刀子似的往领子里钻。
路过潘教授家旧址那扇被抄家时砸烂的木门换了新的却总觉得门缝里还飘着当年的墨香。
潘教授被带走那天我躲在树后看见孙卫东举着红缨枪把块银灰色的上海牌手表塞进裤兜——那表我见过潘教授总用红绸子裹着说表盖里嵌着他亡妻的照片。
街道革委会的小二楼在巷子深处冒着烟。
推开铁皮门门轴“吱呀”一声惨叫惊得墙根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
左右两间办公室里算盘珠子噼啪响成一片有人正用红蓝铅笔在报表上打勾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竟比窗外的风声还急。
那是劳动服务队队长在给街道劳动服务队员们准备结算劳务费发工资。
楼梯平台上王大庆书记的军大衣搭在椅背上铜纽扣在日光灯管下亮得刺眼我刚要抬脚就听见女徐副主任在走廊里喊:“小张过来。
” 她的蓝布棉袄第二颗纽扣松了线用别针别着手里捏着张油印材料油墨味混着她身上的蛤蜊油香飘过来:“出期揭批专刊马文书给你找资料。
”说话间她的目光在我腿上顿了顿像扫过件碍眼的旧家具“会议室暖和你去那儿弄。
” 会议室果然比外头强些墙角的煤炉烧得正旺烟囱上搭着的湿毛巾冒着白汽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熏得更黄了。
我铺开大白纸时看见墙面上留着上个月居民大会的粉笔印“抓革命促生产”几个字被人用指甲抠得坑坑洼洼露出底下的石灰。
马文书抱来一摞文件最上面那张印着“XX罪行录”油墨重得能沾住指纹他搓着手说:“多用红广告色醒目。
对了王书记说要见血的劲儿。
” 毛笔刚蘸满墨后颈突然掠过一阵风。
王大庆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军大衣上的雪化了在地面洇出个深色的印子。
“字要硬!”他的拇指戳着纸面力道大得让纸颤了颤“得像刺刀扎进敌人心窝子!”我点头的工夫看见他领口别着枚褪色的毛主席像章边角磨得发亮背面的别针都锈成了红褐色倒像是块贴身戴了多年的老玉。
写“抓纲治国”四个字时左手按在纸上发颤。
隶书的横画本该像扁担般稳当可“国”字最后一笔偏了墨汁在“玉”字底拖出个蜷曲的勾像极了医院厕所门上那个轮椅符号——上周换药时我盯着那符号看了半晌铁皮牌被人踹得歪歪斜斜却还是执拗地立在那儿红漆剥落处露出黑铁像在嘲笑我裤管里塞的旧棉花。
想补笔时笔尖在纸上洇出个黑团倒把那勾子衬得更清楚了活像块长在字里的骨刺。
画女社员头像时炭笔总往斜里走。
林小梅初中时总借我的橡皮她的辫子扫过我手背带着股皂角的清香。
有次她转过身问我“之乎者也”怎么写阳光正落在她右眼角的泪痣上我忽然忘了要说什么只听见自己的心跳撞得课桌咚咚响。
此刻笔尖在纸上转了个弯那痣就落在画像颧骨下方我赶紧用红广告色盖却越涂越像朵渗血的花。
炉子里的煤块“咔嚓”裂了缝恍惚间竟听见她念课文的声音脆生生的混着粉笔灰的味道。
专刊贴出去那天巷子里的雪冻成了冰壳。
我扶着墙根站在人群外听见卖豆腐的张婶说“这画画得真像回事”正想笑就看见个穿酱油厂工装的身影撞开人墙。
孙卫东的脸比当年胖了圈可眼里的狠劲没减当年他抄潘教授家时就是这眼神一脚踹碎了人家传了三代的青花瓷瓶。
红墨水泼过来时我闻到股铁锈味。
扑上去的瞬间后背撞上板报栏的木框残腿一阵发麻像有无数根针在扎。
红漆顺着棉袄往下淌在雪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映着灰蒙蒙的天。
孙卫东被民兵按在地上时我看见他手腕的上海牌手表——表蒙子裂了道缝指针卡在三点十七分表链上缠着半圈红绳该是后来加上的倒像道勒住时间的枷锁。
“瘸子也配干这个?”孙卫东的唾沫星子溅在我鞋上民兵拽他起来时表链刮过冰面碎玻璃渣嵌进雪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我突然想起潘教授被带走那天手里攥着这块表指节白得像要捏碎它嘴里反复念叨“时辰到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本文地址轮渡上的逆流人生第40章 寒墨来源 http://www.jiwuzhaipei.com
 干翻法外狂徒后我封神了
干翻法外狂徒后我封神了
 满宗绝色我是唯一男修
满宗绝色我是唯一男修
 银霜领主
银霜领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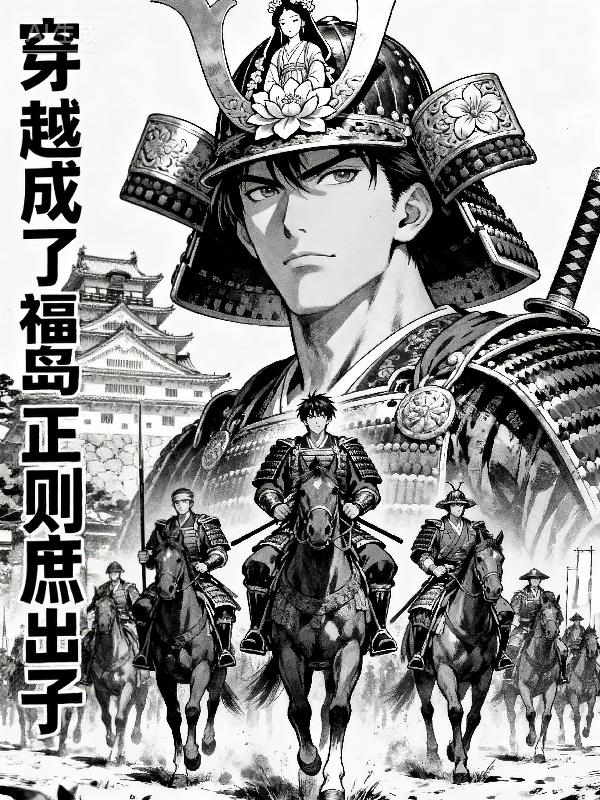 穿越成了福岛正则庶出子
穿越成了福岛正则庶出子
 躺赢仙途我的咸鱼系统逼我无敌
躺赢仙途我的咸鱼系统逼我无敌
 灵韵峰无敌小师弟
灵韵峰无敌小师弟
 领主求生从残破小院开始攻略
领主求生从残破小院开始攻略
 星铠之我的日常生活
星铠之我的日常生活
 三国孙策托孤我截胡孙权基业
三国孙策托孤我截胡孙权基业
 大唐秦公子
大唐秦公子
 道爷我在娱乐圈当公关
道爷我在娱乐圈当公关
 八个姐姐独宠我全是扶弟狂魔
八个姐姐独宠我全是扶弟狂魔
 亡灵法师不是亡灵谐星
亡灵法师不是亡灵谐星
 缘起开局我竟然放走了小白和小青
缘起开局我竟然放走了小白和小青